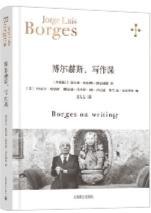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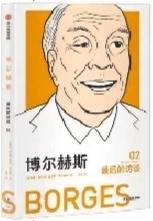
李海卉
距离1923年博尔赫斯出版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已经100年了,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的博尔赫斯的“写作课”新近面世。《博尔赫斯,写作课》这本书回应了博尔赫斯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读者和作者。
博尔赫斯是语言的魔术师。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曾说,没有博尔赫斯,就没有今天南美的现代小说。马尔克斯也说:“我读博尔赫斯是因为他驾驭语言的杰出能力;他是可以教授写作的人,也就是说,他会教你如何打磨语言工具,来用它更好地写作。”
这本《博尔赫斯,写作课》汇集了博尔赫斯教授英国文学课程的完整内容。尽管当时博尔赫斯几乎已经失明,但执教十年的他仍然在课堂上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与纯熟的教学技巧。他作品的翻译者迪·乔瓦尼为他和学生们朗读他的作品,让他在朗读的间隙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解释和评论。在讲课的框架内,博尔赫斯的学识渊博总是显而易见。而且,这种渊博从来没有限制他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博尔赫斯不是为了“炫技”而引用原文,而是在切合讨论的主题时才这样做。对他而言,想法比确切的事实更重要。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会惊讶:他确实记得很多日期,具有难以置信的精确度。要知道,博尔赫斯讲授这些课程时肯定已经无法阅读。因此他引用文本以及他的诗歌背诵都取决于他的记忆,并足可以证明了他极为广泛的阅读范畴。
就这样,博尔赫斯在作家和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之外“解锁”了新身份:博尔赫斯教授。在他的自传中,博尔赫斯写道:“我这一生都不知不觉地始终在为这个职位做准备。这个简单的陈述产生了我想要的效果。他们聘用了我,我在大学度过了十二年的快乐时光。”
博尔赫斯生于阿根廷,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但他同时懂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尽管“他可以用法语流畅地阅读保尔·瓦莱里,用意大利语阅读贝内德托·克罗齐,用德语阅读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用英语阅读T·S·艾略特”,但他创作的主要语言还是西班牙语,并且他在用英语思考西班牙语,对文学母语西班牙语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创新改造。这就是博尔赫斯语言的特殊性,并且他对文字的纯粹性的追求使得这种特殊性更显珍贵。
博尔赫斯是一个世界级的作家,他不断地自我突破,对身处各地的读者,有着重要的意义。博尔赫斯让人们明白,一个人能够直面自己的生活经历,不必为此感到遗憾。”博尔赫斯并不是天生眼盲,他用双眼读过纷纷世间,看过浩浩书海。但是当他的视力逐渐消失时,他并没有为此多作纠结。在1955年底博尔赫斯接受被任命国家图书馆馆长时,双眼已经渐渐失明。他说,“我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身处90万册各种语言的书籍中。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很多的书和夜晚,却不能阅读这些书……我下了一个决心。我对自己说:既然我已经丢失了那可爱的形象世界,我应该去创造另一个东西。我应该创造一个未来,以接替我事实上已经丢失的视觉世界。”
《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收录了博尔赫斯在哈佛大学任职期间与理查德·伯金所做的著名访谈。博尔赫斯曾说,“理查德·伯金让我重新认识自己。”在这次谈话中,博尔赫斯给出了针对自己和他人的文学作品的真知灼见。而辞世前几日,博尔赫斯与他的好友莱库比曾进行过一次私密的访谈,涉及他的生活、爱以及对自己作品的种种思考,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后的访谈”。这几次贯穿博尔赫斯写作生涯的访谈,为读者了解这位20世纪著名的文化巨擘打开窗户。
“我最后一次看清自己的样子大约是在1957年。”这句话简单又残酷,但是却带着一股文学的浪漫,博尔赫斯说到自己失明前看到的最后的颜色是黄色,并写过一篇名字叫《老虎的金黄》的小说,好像失明是一种无法阻止的命运。在《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中他说:“你也许会失去某些东西,但同时也会得到一些东西,也许只是单纯的丧失感,但那至少也算是某种天赐之物。”70岁时,博尔赫斯说:“有许多年,我曾经想,只要变化无穷、标新立异,也许会成就一页好文字;如今,年过七十,我相信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诗人西川说:“我们的特点,往往不是由我们的优点造成的,而是由我们的缺陷造成的,写作中尤其是这样。”作家余华说,读博尔赫斯的小说时,我们身处迷宫之中,他成了文学迷宫的创造者,并且乐此不疲。我们在博尔赫斯的“写作课”中细细探寻,随他找到迷宫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