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长篇小说《不舍昼夜》:让微光照亮“不彻底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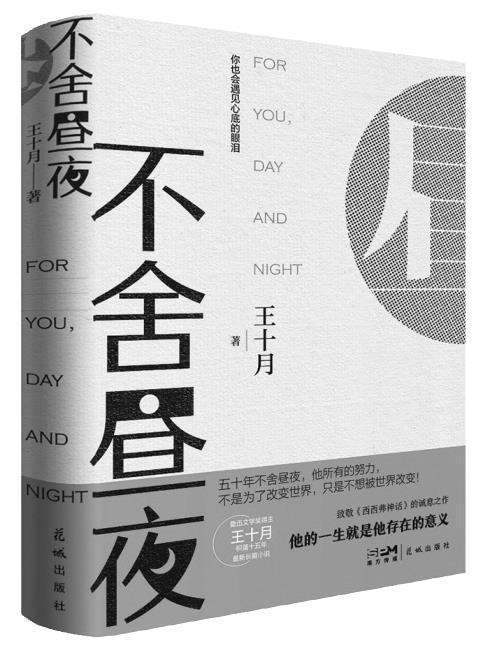
□李 瑄
《不舍昼夜》是王十月积蕴15年的重磅力作。小说以“70后”主人公王端午的人生轨迹为主线,详尽描绘了从20世纪70年代至2023年近半个世纪里个体生命的成长历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透视社会的演变,折射时代的更迭。
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者,王端午身上凝聚了千千万万个打工人的优点和弱点:贫困、敏感、自尊,极力融入社会,却又对社会保持警惕、怨恨家乡;永远被家乡裹挟,抓住每一个机会逃离,却又被社会的浪头打回原地,在义气中背叛,在堕落中飞升,在爱时掺杂着恨,在生时思考着死。总的来说,王端午就是一个“不彻底的人”。这一点,王端午的妻子冯素素也看出来了,在她眼里,王端午“想做好人,却又干了坏事,想做坏人又做得不彻底”。他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有时温暖有时冷酷,有时纠结有时通透,有时善有时恶——当然,大多数的“极致”并未表现在行动上,更多地是发生在内心里。王端午是如此平凡、真实而普通,如你,如我,也如他。
小说中最令人称奇、也是最具现代主义特质的一点,是作者在王端午“害死”弟弟之后,让他在哥哥的脑中复活,并与之终生相伴。因此,在王端午身上至少拥有两重人格,在改名为李文艳和王端之后,又拥有了另外两重人格。终其一生,多重人格一直在相互撕扯、争夺,互有胜负,但最终王端午还是回归了最初的自我,寻找到了精神的根。与此相似的还有王端午的妻子冯素素。冯素素是书中极具个性的人物,她深受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影响,喜欢以“冯素素认为”“在冯素素看来”之类的口头禅与人沟通,仿佛冯素素不仅仅是她,还代表了某一类人。这时的她是复数的、理性的,而在成为王端午的妻子后,她会不自觉地以“我”为主语来进行沟通和表达,这时的她是单数的、感性的。她好像在体内安装了一套“装置”,可以随时在两种身份之间切换,这种特殊的设定使得冯素素的人物形象独特鲜活,风姿卓异。
在小说中,王端午的成长与他的阅读史密切相关,在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上,他用以反省的思想资源也来源于他读过的那些书。在王端午提到的几十部书籍中,非常重要的是《卡门》《卡夫卡传》《西西弗神话》《存在与虚无》《荒原狼》这几部,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西西弗神话》,这是王端午用以观照世界和解剖自我的主要武器。西西弗的故事来源于希腊神话,据说因得罪了诸神,西西弗被罚推一块巨石到山顶。巨石沉重,山坡陡峭,每当他用尽全力即将抵达山顶时,石头又会滚落山下。他只好重新再推一次,日复一日,永无止境。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且无望的重复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在中国神话中,也有一个与西西弗十分相近的人物,那就是吴刚。吴刚被罚在月宫砍伐一株桂花树,其树随砍随合,同样也是以一种永无休止的重复性劳动对其进行惩罚。我们可以想象吴刚是快乐的吗?按照加缪开出的“药方”,吴刚在砍树的前中后期,都有足够的机会对其命运进行反思,并从中发掘出乐趣和意义——即使最终他发现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什么意义。
《不舍昼夜》中的王端午,似乎可以被解读为当代的吴刚、中国的西西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从故乡到异乡,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从独身一人到为人夫为人父,从想做一个不一样的自由的人到从心底里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平庸的凡人,王端午在不同的身份中反复跳转,在无尽的漂泊、劳作、谎言、丧失、病痛、愧疚、绝望中,不断反躬自省,抖落尘埃,艰难跋涉,接近自我。尽管他最终发现世界是荒诞的、生活是残酷的,但最终他还是爱着这一切,不离不弃,不舍昼夜。这爱,稀薄而强大,隐蔽而闪耀,微弱而亘古。
王端午憎恶他的故乡,但他后来发现故乡的野花与风景其实很漂亮;王端午怨恨他的父亲,但他后来也承认父亲其实是爱他的。在王端午的朋友圈里,既有刘祖之这样背刺朋友的小人,也有李中标这样温厚、诚挚的一生之友。处理弟弟和李文艳的死亡事件中,王端午主动揽责,抱愧终生,何尝不是他对人类的爱、对人性善的认同在隐秘地发挥着作用?对他来说,最大的安慰来自于热烈的爱情,无论是宋小雨、阿霞还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冯素素,这些女性都让王端午体会到了爱情的甜美、丰盈与复杂。在和冯素素的爱情中,王端午甚至悟出:“爱,才是对死亡最有效的反抗。”
在《加缪手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荒谬当道,爱拯救之。”爱就是荒诞世界里那道最珍贵、最迷人的光。王十月在王端午身上,倾注了最多的情感与最大的创造力,为当代文学的文学景观贡献了一个新鲜的形象:“不彻底的人”,或可与屠格涅夫的“多余人”、加缪的“局外人”互相参照。读到小说的结尾部分时,我一直在猜想作者会给王端午安排一个怎样的结局。如果要是由我来写,可能会选择让王端午自我了结,毕竟在他身上积压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很难处理他继续活下去以后的生存问题。但作者选择让他在直播中忽然“软软地瘫在地上”,“他最后的知觉,是裤裆一热,一泡尿没有憋住”,这种处理足够让人同情和遗憾,他的生命止于生活的终结,而尚未抵达哲学的终结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