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礼上的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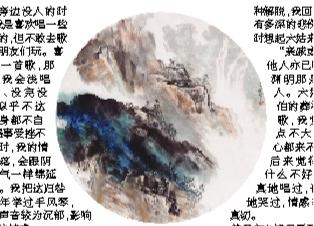
□邓跃东
旁边没人的时候,我是喜欢唱一些小曲的,但不敢去歌厅跟朋友们玩。喜欢上一首歌,那几天我会浅唱低吟、没完没了,似乎不这样浑身都不自在;遇事受挫不顺利时,我的情绪低落,会跟阴雨天气一样绵延很久。我把这归咎于早年学过手风琴,那种声音较为沉郁,影响了我的情感。
阴晴圆缺,喜忧交替,日子就是这样不断翻转的。但是,常有人说我放不开,爱不起也恨不起。后面其实还带着一句话:拿不起也放不下。我不大理会,依然我行我素。
前不久,我大伯去世,停灵的最后一晚请来戏班子,热闹了半晚上,班主还问有谁上台唱歌吗。这个情景,我们是不好参加娱乐的,最多坐在台前看看。想不到,静默一阵后,我六姑走上前接过话筒,大大方方唱了起来!
六姑是大伯的胞妹,六十多岁了,在农村生活,这几天都在灵堂忙碌,不时痛哭,好大一颗的泪珠,她用手背去擦拭,其他人都哭得委婉。我从未听六姑唱过歌,她唱的是《母亲》,就是阎维文唱的那首熟悉的歌,嗓音洪亮,气势惊人。六姑怎么唱这样一首歌呢?大伯比她大很多,难道充当了母亲的角色?过去爷爷奶奶受批斗被关押,好些年都是大伯在操持这个家。也许,六姑没有这样想,她就是想唱一首歌,想唱就不用分场合。
唱完后,大家鼓掌叫好,竟要她再唱一个。六姑笑了笑,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的唾沫,又唱了起来。这一次她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没有配乐,独自清唱。这感情跨度太大了吧,一下从家里跳到了水里,要是身后的大伯听到会怎么想!
第二天的送葬路上,六姑的哭声盖过了所有的行人,从此再没有那种熟悉的爱怜了,她心里无比地悲伤。后来下起小雨,六姑没有打伞,雨水泪水,泥泞一身,其他人不停地甩着裤脚上的泥巴。可能,只有这样在雨中淋漓哭喊,她才能释放自己的悲伤。
午餐时,我看到六姑跟客人坐在一起,她给人不停夹菜,叮嘱他们注意身体,自己还喝了一杯酒,满面红光。
大伯病得久,他的离去对大家是一种解脱,我回家后没有多深的悲伤,倒不时想起六姑来。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陶渊明那是说外人。六姑在大伯的葬礼上唱歌,我觉得有点不大好,伤心都来不及呢;后来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她认真地唱过,也认真地哭过,情感丰富又真切。
曾经在电视里看到,黄宗江去世时,家人按照他生前的嘱咐,在丧礼上循环播放《九九艳阳天》,那是他编剧的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主题歌。他最后留给大家一片艳阳。
读书得知,弘一法师临终回顾一生,写下 “悲欣交集”的四字遗书,可见人一生是大悲大喜相伴的,不必克制。但是从书本到现实,隔着遥远的距离。
在农村,都是本分守己、息事宁人,荣辱悲欢压在心底,生计压身呢,哪能纵情悲欢。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被这样的观念影响着,矜持谨慎,隐忍压抑,为着一个满足颜面的目的。
六姑的炫亮显现,打破了陈见的束缚。为什么能够呢?也许是长年的劳作多感,需要一个契机去展现,她们心里也有歌,唱了心情舒畅;同样,生活的悲伤是避免不了的,积压太多太久,就要及时释放,跟人倾诉,或痛快哭一场,身心反而正常了。
经常欢笑,身心健康,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我在此时,却想起了一场庄重的哭来。前辈作家谢璞先生故去前两年,他的长子先他而去。白发别黑发,自然令人悲伤不已。办完丧事,谢老想找个地方好好哭一场,无奈杂事缠身,几次出行未果。直到把事情料理完,才抽出时间,一个人来到晓园公园深处,扶着垂柳,边哭边诉。哭完后,他面若无事,回家继续读书写作。
生活不能缺少笑,也不能缺少哭。经历了大悲大欢,人生才能说宽广,才能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