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总是这样让人入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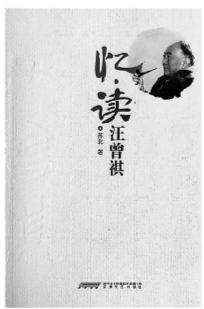
读《忆·读汪曾祺》这本书,我本不想从中得到什么。之所以读,只是因为喜欢,喜欢看看苏北笔下的汪曾祺。故而我抱着相当随意的态度悠游其中。好似一朵白云在辽阔的天空里高悬着,有微风来它就走一走,有大风来它就跑一跑。我正如那朵白云,这本书就是一整片天空。我沉浸在它的故事里,有意趣横生、乐而忘返之感。在这本沉淀着旧时光又充满款款深情的书中,一个让人喜欢的老头形神俱现。
他喜欢逗小孩,与小孩子对话时充满童真。他喜欢邀请年轻或年老的朋友来家里,顺便尝尝自己的厨艺。他打趣一道出行的作家朋友,用一首首打油诗。他喜欢写字,也喜欢画画,喜欢把自己的字和画赠予有缘人。他喜欢沈从文和废名,喜欢自己,喜欢自己的文章并且对自己的文章充满信心。他喜欢游玩,游玩到哪里就把笑声欢乐带到哪里。他喜欢把自己的创作心得与体会,巨细无遗地分享给年轻一辈的作家们。
苏北就是这年轻作家中的一个。他回忆与汪曾祺早年过从的美好时光,他讲述读汪曾祺作品的诸多体会。书虽比人长寿,人却也一直活在书里。本书虽分成忆与读两部分,然而读者不难看出在苏北这里,忆与读、读与忆常常是纠缠不清、不分彼此的。忆汪曾祺,如读他的书;读他的书,如听他说话。“这些书内容实际上都是重复的,里面的文章我也读过,可只要有一点新变化,哪怕是编法上有些别致,仿佛上了瘾,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给买回来。”是上瘾,也是痴迷。我忍不住想象苏北在汪曾祺作品中流连的画面,以及他站在汪曾祺著作书柜前一只手伸进去探寻、抚摸的情形。“这些年来,我沉浸在汪先生的文字里,乐此不疲。这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入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是苏北在后记中写到的。能找到愿意一生追随的前辈作家,是年轻作家的幸运。这种幸运的得到,需要机缘、巧合、际遇。有前辈作家其人其文的精神引领,其润泽与灌溉对年轻人来讲是无处不在的。然而,追随不是亦步亦趋的跟班,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在模仿、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模样。
汪曾祺的热,我是深知的。这种热之精神源头不在其他,而在汪曾祺先生身上。他全部的身心,都在充满人气和温度的世俗中。正因为此,其作品的热也就顺理成章。苏北说:“有的作家‘人一走,茶就凉’,而汪曾祺的价值却越来越凸显,身后越来越热闹。”如果汪曾祺尚在人间,大概会乐于欣赏此番热闹的。因为充满天真气与情趣的作家,本身就是大俗人一个,焉有不凑热闹之理?想当年,汪曾祺就是一个喜欢热闹之人。若非如此,苏北是否能够拥有与汪曾祺如此美好的缘分,也是很难讲的。“汪先生在晚年,对青年人特别友好、关心,为许多青年人的新书作序,多有褒奖和扶掖。”
自从汪曾祺去世之后的二十几年来,苏北一边回忆和他的过往,一边读他的作品。且忆且读且写得多了,如何评价汪曾祺反倒成为一桩难事。从喜欢并手抄汪曾祺的作品,到与汪曾祺结缘后时有过往,苏北的身份从读者渐变为朋友、抹去年龄差距的朋友,可称之为“忘年交”。于是,汪曾祺从书里走出来,走进苏北的生活中。这是汪曾祺双重身份逐渐累积、叠加的过程。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的交集过后,他在苏北的世界里日渐清晰。可以说,汪曾祺就是他的精神标杆。
品评汪曾祺的《夏天》时,苏北说:“他笔下的这些花草,栀子花、白兰花、牵牛花,无不充满生命。是灵,是透。该简就简,该繁就繁。最简单的事物,就是美。能写得透亮、清澈,云影、阳光、树影,都倒映进去。汪先生的思维是跳动的,他的语言和思绪是敞亮开阔的。汪先生是能够说明白话的人,他对语言的把握是清楚的。他心灵里有哪些东西,他准确、明白地说了出来。”面对汪曾祺这样一个高蹈的精神标杆与巨大的精神体量,苏北的说与道想必是终其一生的快乐之事。
不必着急说,应当慢慢说,这才是苏北言说的姿态。即便是反驳别人对汪曾祺作品的论断,苏北也是慢条斯理的。听苏北讲与汪曾祺有关的故事,如读一部不设结局的长篇小说。引汪曾祺的文字,全文照抄,细细品读,如对亲密友人倾诉悄悄话一般,不涉任何的理论。提及汪曾祺的一言一行,一个个画面的再现,如播放电影片段,有一股慢悠悠地淌进心田的暖流在。这种不矫揉造作、不板起面孔、不正襟危坐的态度不正是汪曾祺给予苏北的精神给养吗?
《高邮·高邮》写到汪曾祺故乡高邮的经历,先写鲜藕、棱角、芋头,再写茶炉子、大淖,随后写盛开的晚饭花,接着写一座充满活力的“民俗博物馆”,最后写汪曾祺故居与纪念馆。持续并沉淀长达二三十年的忘年交情为背景的探访,必然是慢慢走,慢慢讲,慢慢感受的。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