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神农架是我生命开始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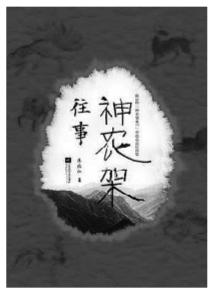

作家简介 陈应松,1956年生于湖北公安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长篇小说《森林沉默》《还魂记》《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等100余部,《陈应松文集》40卷,《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选》3卷。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湖北文学奖等。2015年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文化名家”称号。
神农架之于陈应松,正如湘西之于沈从文,商州之于贾平凹,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
当今文坛,湖北作家陈应松以一系列神农架小说而独树一帜。他在神农架山野里掘宝,写出一系列小说和散文,告诉世人神农架之神。与江苏颇有渊源的是,不论是其神农架系列小说的第一篇《豹子最后的舞蹈》,还是为其斩获鲁迅文学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陈应松几乎所有关于神农架的重要小说都发表于《钟山》,而新作《神农架往事》和《森林沉默》也已经或即将在江苏出版。
上个月,因第二届扬子江作家周,陈应松应邀来到南京。用他的话来说,年过花甲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写作”的年纪,面对记者提问,他的回答都很坦诚,“我感觉要把小说写好,就像马尔克斯说的那样,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就是让你周围的朋友、亲人、喜欢你的人更喜欢你,如此而已。”
回到森林有种奇怪的亲近感
“我的人生和创作生命都是从神农架开始的。”陈应松这样开启了故事的讲述。
去神农架挂职那年,陈应松44岁。人到中年,写了那么久,也发表了那么多作品,但似乎并没有得到文坛的认可。“文坛并没有把你当一回事儿,感觉你是可有可无的,说白了就是还没有‘火起来’。”陈应松回忆道,“别人又说,陈老师你小说写得这么好,怎么又没得奖,什么都没有,你是中国文坛的第一大冤案。”这话刺激了他。
那时候,陈应松生活在武汉作协的大院里,每天接触的都是作家,有成名的方方等,更多的是没有成名的。“满头白发在那里晃来晃去,很落寞。当你不是著名作家的时候,人的内心是非常自卑的。”他自嘲道,“人即使到老了,也还有虚荣心。何况是作家,作家的虚荣心是最强的。”
半是逃离,陈应松离开了城市,想去远方走一走,去体验陌生的生活。而此时,神农架这片原始森林的景色和故事,带给他极大的震撼。
陈应松第一次去神农架是十月份,那里已经下雪。满山都是脱光了叶子的野柿子树,“红艳艳的,漂亮极了。真的非常亲切,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我来过一样,好像就是过了很久,我要回来,那一种感觉。”陈应松形容他到神农架是“还乡”:“我们的祖先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所有的人回到森林的时候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感觉:你有一种非常奇怪的亲近感,或者说人类身心的‘遗传返祖’现象。好像我们又变成了‘猿’,又可以在森林里生活那样一种感觉。”
除了这样一种亲切感,从小在平原长大的陈应松,在神农架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了解深山中的居民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这里的生活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不像别人的动物小说、寓言小说里所想象的,森林里是一个充满了童话的世界。不是这样的。”
神农架的故事两辈子都写不完
关于神农架的一系列书写,陈应松将其归纳为“很偏僻的题材,很偏远的故事,很偏颇的感情”。
神农架有一种树叫娑罗树,它的果实是一味中药,“大概卖两块钱一斤,一棵树可以卖一两百斤。这些人穷疯了,他不是爬上树去摘的。那么粗的树至少有50年,他从中砍断了以后,在地上摘果子。我看到这种行为非常痛心,关于贫穷的痛心。”
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的第一篇《豹子最后的舞蹈》,就是他在神农架听到有关“最后一只豹子”的故事后,深受触动而写下的。过去我们读过一篇课文叫《打豹英雄陈传香》,讲述一个18岁的女孩子赤手空拳把一只豹子打死。陈应松发现了这篇课文背后更多的故事。
“自从陈传香打死了这只豹子以后,神农架从此没有看见过豹子。我大概有两个月无法从这种情绪中拔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只豹子的时候,它多么孤独、可怜。而且把它解剖了的时候,发现肚子里什么食物也没有。你不打它,它也会饿死。这些故事对我的触动太大。”
这种有别于文明世界的野性、野蛮,甚至近乎狂暴的东西,蕴藏于神农架这片神秘的土地,它们激发了陈应松的创作灵感。“你是真正的有所触动,不像我44岁以前,写小说就相当于编造的、杜撰的。这些故事来源于生活,只是看我用什么感情把它写出来。”他说。
现在,陈应松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神农架的工作室中。“神农架这里的故事我写两辈子都写不完。”除了神农架的故事,陈应松还在书写平原和湖区生活的经验,“我下一部长篇又是写平原的,交替地写。毕竟整天在那种鬼魅横行的世界里穿行,人的精神还是会太紧张。”
“我也就是一个工匠”
陈应松最初踏上文学之路是因为写诗。在他当知青的时候,出于对诗歌的喜爱,陈应松开始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诗歌。
因为这一段写作经历,陈应松得以于1985年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深造,并开始小说写作的生涯。这些插班的同学都是写作的,但是写小说的稿费更高,眼见着那些写小说的天天下馆子,还请他们吃饭,搞得陈应松这些写诗的人很没面子。所以陈应松也开始写小说,并且一出手就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这与他诗人出身语言好的优势,以及小说写作先锋的态度有关。
“我认为50后是文坛最先锋的一批作家,而且他们是永远先锋的,在写作上是真正的求新求变。有时候你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50后的作家,有一种持续的创造力和激情、冲动。”
这样一种持续的创作动力究竟从哪里来?
“我认为,就像一个手工艺人一样,你从事了一辈子这样的事,你到老了还是得干这个活,别的活你肯定干不了,是吧?我采访过的很多老工匠、老师傅,作品是做得越来越好。文学是一样的道理,它也是一种手工操作,我也就是一个工匠。当然年纪越大,内心更平静,他那种持续的写作、创作的激情,在他的身体里就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本能的冲动了,不像年轻的时候,亢奋写作、激情写作。现在这种创造力保存得很好,慢慢地释放,没有空仓的时候。”
陈应松的最新作品是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森林沉默》。评论家李敬泽曾评说,“陈应松欠中国文学一篇森林。温带的、浩瀚的、确切的、威严的、创世和永恒的森林,这是他命里该写的,也很可能是只有他能写的。”陈应松用《森林沉默》还了债。李敬泽读后称,“我们有了一片与现代性、与喧嚣人事相对峙、相辩驳的森林。”
这是陈应松第一次专门写森林,在“风景描写”淡出小说创作的当下,陈应松不吝笔墨书写着森林的原始奇异景观,不但丰富了小说的审美意蕴,更有助于借风景,完成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陈应松非常喜欢托尔斯泰的这句话:人一旦到六十岁,就应该进入到森林中去。“去森林不是为了写作,而是为了生活,安放自己的肉身。”陈应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