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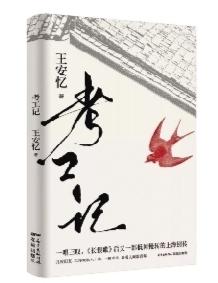
《考工记》原是战国时期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献,记载了各种工艺的规范及体系,而王安忆所著的《考工记》,却是带着历史的长焦,描述了一位十里洋场“小开”,逐渐蜕变成普通劳动者的过程。
出身世家的陈书玉,历经战乱,回到了考究而破落的上海老宅,与合称“西厢四小开”的三位挚友,憧憬着延续殷实家业、展开安稳人生。然而,时代大潮一波又一波冲击而来,文弱青涩的他们,猝不及防,被裹挟着仓皇应对、各奔东西、音信杳然。陈书玉渐成一件不能自主的器物,一再退隐,在与老宅的共守中,共同经受一次又一次的修缮和改造,里里外外,终致人屋一体,互为写照。半个多世纪前的“西厢四小开”,各自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他们是千万上海工商业者的缩影,是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沧桑注脚。
据该书出版方介绍,继《长恨歌》之后,《考工记》是王安忆书写的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而“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似乎意味着,当代史也可以跳脱出当代日常、世俗民间,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物的经验,即使与人的经验息息相关,却比人的历史存在更长远。
王安忆以一贯细腻节制的笔触、熨帖人心的语言,审视这些人物、老宅与城市的命运关系。人物沉浮与老建筑的存亡紧密相连,时代的起落更迭促使陈书玉个人的成长与嬗变。
不说一字多余的废话,文字凝练简练是一种本事,这种本事对作家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说“废话”的本事。前者可以通过自觉的刻苦训练达到,后者无人能教,即使自己有所领悟,也难以做到。而《考工记》经常出现这类“废话”。陈书玉深夜回家时,在路上“一只肥硕的老鼠从脚下蹿过去,他原地跳一跳,放了生。” 没有“放了生”这三个字,文句一样通顺,意思一样明白。但是有了这三个字,就立时将一个小动作的内涵大大扩展了。
这类“废话”在《考工记》里随处可见。“不论谁在朝,皇帝还是总统,都要有百姓在野。”“闲暇开始让人生厌,就预示假期即将结束。”
《考工记》另一个令人惊奇之处,是对器物的描写。小说写器物并不稀奇。《考工记》写器物之所以令人惊奇,是其刻画描摹达到了极其细腻和精确的地步。作者似乎有意识地以此来呈现时代特征、烘托环境氛围。
在书中,陈书玉居住的是曾祖在乾隆年从一官员手里买下的豪宅。描写和交代这座历经两百年的中国老宅,自然会涉及古建筑学、木工技艺甚至地砖工艺以及流行纹饰(如暗八仙)等,难免会使用到文物古董等很专业的术语。作者使用这些术语的时候很自然贴切,毫无做作之感。写到二十世纪初器物如美孚火油、麂皮沾牙膏擦玻璃灯罩、培罗蒙成衣券,甚至提到奶娘也说诸暨籍奶娘(诸暨奶妈清末到二十世纪初在上海很流行),提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也是用那个时代的译法“翡冷翠”。小说的时间跨度从抗战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长达半个世纪,器物描写几乎无一不细致而精确,可见所下功夫之深。
王安忆,当代著名作家。1977年始发表作品,迄今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天香》《匿名》《考工记》等十四部,《王安忆中篇小说集》八卷,《王安忆短篇小说系列》八卷,散文集、剧作及论述等多部,逾六百万字。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项国内外文学大奖。
书评
《考工记》:“万物皆非,唯有人是”
李浩
“一唱三叹,《长恨歌》后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这是《考工记》封面上的一句话,“别传”一称,颇有从一人一宅之史见出一座城市之史之意。关于上海的书写,曾经颇为流行的是“上海怀旧”和上海滩传奇的建构,这两类书写却并未真正触及上海这座城市骨子里的精神,而真正把握了二十世纪上海的市民精神并成功地完成了这一类书写的当代作家,当数王安忆和金宇澄。“他们关心的不是上流世界或国际都市的传奇,而是这座城市的‘芯子’,它的真精神,它的世俗情感背后的神圣价值和道德热忱”(刘复生:《上海故事的“前世今生”》)。如果说《长恨歌》和《繁花》共同建立了一种新的上海书写传统,那么王安忆的新作《考工记》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赓续。
“我将小说题作‘考工记’,顾名思义,围绕着修葺房屋展开的故事。又以《考工记》官书的身份,反讽小说稗史的性质……这个人,在上世纪最为动荡的中国社会,磨砺和修炼自身,使之纳入穿越时间的空间,也许算得上一部小小的营造史”(王安忆语)。在这部“小小的营造史里”,王安忆考的不仅是一座老宅的历史,更是一个人、一座城市的历史。小说从1944年写起,彼时由于偶然的机缘前往西南求学的主人公陈书玉刚从重庆回到上海的祖宅,因为战乱,祖宅人已走净。归来次日,陈书玉首先找的不是关系疏离的家人,而是要好的几个故友,人称“西厢四小开”——父亲开律所、自己习西洋油画的奚子,延续祖业从木器的大虞,家里做过洋人生意、后渐渐没落的朱朱,以及祖先曾经营码头船号,后世靠盘得的银子过活,还有一家祖宅的陈书玉。四人因为共同的兴趣和相近的家庭经济状况结缘,但昔日挚友也未能避免被动荡的时局冲散,或因家庭或因个人选择,各人走上不同的道路。奚子投奔革命,朱朱携妻子去了香港,大虞回到乡下,唯有陈书玉一人留在了上海城与老宅及宅内的上辈老人相守。数十年过去,人与老宅同在风雨中飘摇,也就这么走了过来。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走来,陈书玉和老宅经历了一个个深刻改变社会进程的历史事件,但在《考工记》中,它们却淡去,只是不声不响的背景。尽管人与老宅的命运和它们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但在作者笔下,却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之感。《考工记》要着意呈现的,只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小事件,这是作者一贯的小说观。“现实这么发生,历史这么进步,那么多重大的事情,小说却只是小人小事,古人说是‘稗史’,但是和人、生活贴得很近”(王安忆:《小说的常理与反常理》);“局势在改变,但波及他们,大世界里最小最小的因子,就溃散了能量,平息下来,归为原状”。 在这里,历史并不显得沉重,它给人的感觉却是冲和平淡,把“重”写“轻”,或者说用“轻”来承载“重”,于是,平淡中也有了至味。这种至味,体现在历史变动中的那些“恒常”中,《考工记》中的生活,似乎有恒常的性质,像水一样,无论从谁家岸边过,都一径向前去,这里断了,那里又续上。
这种“恒常”当然不单指向日常生活,更指向在这个不停变化的世界中经久不变的人心。王安忆曾借用过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的说法,将小说视为“心灵世界”,现实世界只是为这个心灵世界提供材料的。在这个“心灵世界”中,她要做的绝不只是简单地还原出现实世界,而是要“呈现大时代中人与物的恒常经验,甚至可反刍至天道自然的原理,由此逼近当代历史与现实人生更为本质的暗示”。
在《考工记》中,无论是在时代中飘摇、渐渐衰颓的百年老宅,还是叵测跌宕的人生遭际,都只是她所采用的材料,通过这些,她要“逼近”的是——陈书玉将朱朱的事情叙给大虞听,叙到冉太太一节时,大虞所说的,“人不分贫贱贵富,是以性情分……世上的性情归根结底只有两种,一种厚,一种薄”;是旧历年来临之际,大虞来看他,两人一上一下,都是一惊,此时作者所说的,“万物皆非,唯有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