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的是非功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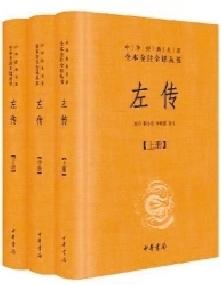
俞晓群
■提示
“白话”一词颇多歧义,此处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言,仅指白话文。说起百余年来文言文与白话文种种议论,妇孺皆知,无需我再多言。只是此事反射到出版领域,再回缩到我小小的书房中,望着书架上那百余册挂着古典名著白话、全译、今译、注译、选译、详译名目的书籍,还是引起我一些思考。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旧三厄,新三厄》,讲到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文中说,除了水火兵虫之外,古书有三大厄。首先是清陆心源所言:“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后面两厄是鲁迅提出来的,一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再一是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当时循着鲁迅的思路,我斗胆提出,时下古书出版存在“新三厄”的现象,即白话、简体、网络版三项。单说白话一项,有观点说“今人好译古书而古书亡”。回忆当时的思考,我是从两个方面看的:正面看白话有利于了解中国历史,辅助学习文言文,普及古代文化知识。负面看文言变白话的副作用,首先它使文言有了消亡的危险;其次在文白对译的过程中,丢失的东西太多,如古诗词根本不能译成白话,文言文固有的简洁与韵味也是不可替代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到鲁迅倡导新文学,反对年轻人读中国经典,批评有些人食古不化的旧事。那是因为鲁迅的古文底子极好,才有资格说那样的话。施蛰存先生在《庄子与文选》一文中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其实不通文言,一定会影响你的口语表达及白话文写作。我早年读书环境不好,后来总结时常常会说,那时无书可读或读书太少。那么哪些书读得最少呢?排在前面的当然是古文、古诗词了。到了花甲之年,再回忆那一段先天不足,导致的后果有二:一是后天的语言枯燥或叙事啰嗦,常常找不到恰当的词语表达;二是写作时提笔无字或平铺直叙,会使用的字词太少或流于成语、俗语一类句式,文字词不达意,文章平淡无味,缺乏文采与韵律感。后来埋头读书做过一些补救,但“童子功”是很难补回来的。
我记得那时中小学课本中古文、古诗词数量很少,学校没有太多的教学要求,师长却时常提醒我们,篇目少更要能够背诵。诸如《陈胜起义》《曹刿论战》《捕蛇者说》《卖炭翁》《丁督护歌》《大车扬飞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至今不忘。父亲还命我背诵《古文观止》中《郑伯克段于鄢》《唐雎不辱使命》《五柳先生传》等篇目,使我的古文底子略好一些。没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却占了便宜。那张语文考卷上有古文今译两道大题,正题为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一段古文,二十几分;附加题为班固《汉书·高帝纪下》中一段古文,三十分。刘邦临死前与吕后的一段对话,其中名句:“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此事堪堪称奇,就在高考前不久,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书柜前,翻开《汉书》为我讲解过这一段故事,没想到它们竟然会出现在试卷中。
在父亲送给我的书中,有几册文白对照的古书,书上有他的钤印。一本《论语批注》,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编,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还有一套《史记选译》上、下两卷,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史记选译》小组编,序言中说,小组人员由战士、蹲点干部、中华书局编辑组成,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再有一本《史记选》,王伯祥选注,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知青的时候,我去铁岭务农,临行前父亲把它放入我的行李中,我一直保存至今。
相对而言,我的书房中文白对照的书不是很多,有些规模的大约有三套:
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岳麓书社开始出版的《古典名著今译读本》十几册,相应的还有一套《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二十几册。两套书都是小开本纸面精装,它们面市较早,阅读方便,很长时间是我案头常翻常查的书,对我早期学习古代典籍帮助很大,至今我仍对那一代校编者心怀感念。
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降,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起编辑《古籍今注今译丛书》,最初是12种,后来达到41种,再后来增加到56种。作者中前辈名家极多,如屈万里、马持盈、南怀瑾、陈鼓应、杨亮功、毛子水。王云五在序中谈到缘起,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国学小丛书》,作者有陈柱、谢无量、胡朴安、周予同、吕思勉、钱穆,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书目如《中国诗学大纲》《诗经学》《荀子哲学》《楚辞新论》《孔子》《孟子》《中国八大诗人》。但王先生觉得《国学小丛书》不是原典全本,普及效果不好,成为一个缺憾。因此发起“今注今译”出版项目。他希望能有多家出版社合作推出,但无人响应,最终只有台湾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仅有《史记今注》六册没有“今译”,注释者马持盈认为篇幅太大,而且注、译相通,不必再多占篇幅了。如今这套书已成名著,内地有多家出版社购买版权,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重庆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三是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纸面精装,在选本、规模、印装许多方面,已成为古籍白话出版的翘楚。我存有一套九册《史记》全本全注全译特装本,黄色缎面装帧,巨大一箱,分量极重,附赠一双镇纸,上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品读如此“贵重”之书,很容易伤到手腕。另外中华书局还有一套《中华经典藏书》也是文白对照本,选书极好,我买过几种,后来发现是节选本,但只在前言中说明,没有在书名中明示。凤凰出版社有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陆续出版一百多种,参与者前辈名家不少,如周振甫、许嘉璐、黄永年、张培恒、金开诚。
最后再说几段难忘的故事:
一是我存白话版本最多的是《周易》《春秋左传》,仅言《左传》,最让我喜爱的是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春秋左传词典》《白话左传》,还有沈玉成《左传译文》。这几本书我都存有两套,一套在家中,一套在办公室。按照杨先生的观点,重要的典籍应该有“三件套”:注释、词典、白话。此套书是一个典范。记得我读《左传译文》时曾向中华书局胡友鸣请教,他说这是一本很难得的好书,一是《左传》《梦溪笔谈》一类跨学科著作最难注译,二是大学者肯做此类事情,大不同于泛泛之辈,对他们是雕虫小技,对读者就是难得一见了。
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白话聊斋》,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初是上、下两册,后来又出续本、全本,总共印了二百多万册。翻译者是出版社的几位老编辑袁闾琨、刘刊、陈志强、邓荫柯等,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老领导,又都是各方面的专家,能策划、能动手。此书上市后不断再版,出版社挣了大钱。那时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如此生动一例,很让我震动。
三是整理书籍时发现,许多注译本都是老师、作者或朋友送给我的,让我难以忘怀。一是孙振声《白话易经》,内部印刷,上世纪八十年代周山送我,成为我的启蒙读物。如今已翻烂,还是不肯丢弃。二是陈广忠《淮南子译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请陈先生写《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两淮文化》,他赠我此书,也是我的启蒙读物之一。三是赵吕甫《史通新校注》,王充闾送我。王先生是看过我的文章《二十四史五行志丛考》,发现其中一条错误,就把他自己的书送给我,夹上纸条,标注出正确的说法。四是陈学明送我南怀瑾《论语别裁》二册,复旦大学出版。那时南先生的书刚刚进入内地,争议之声不小,阅读中我还是受到启发,知道书还能这样写,孔子还能这样评说。五是王之江送我《日知录集释》《遵生八笺校注》,前者影响我一生的写作风格。六是沈放送我《春秋左传词典》,他说这是一本很好玩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