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意义演变的人类学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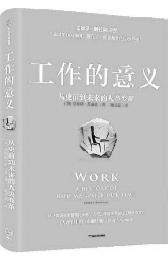
史冬柏
提示
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一度为全民热议,或许因为它触及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深层话题,那就是思考工作的意义。尽管人们向往着“诗和远方”,但现代社会确实让大多数人难以将工作和生活截然分开。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似乎是,许多人把工作当成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在工作场所中搭建生活场景。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的《工作的意义》,其实是个听起来略带误导性的题目,因为作者想做的并不是为工作辩护,而是展开人类学的考察,告诉我们工作的意义并非从来如此,以及工作是如何一步步取得今天这样的地位的。
工作在今天的人类生活中占据着近乎“神圣”的地位,它不仅关系到养家糊口,而且在人的社会化生存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工作的意义》提醒我们,在人类历史95%以上的时间段内,工作的地位其实都没有现在这么重要。
工作时长比现在少,闲暇时间比现在多。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过上了这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在当时,以非洲的朱霍安西部落为代表的很多狩猎采集社会,往往每天只采集当天所需的食物并感到心满意足,而对储存食物以备不时之需并不上心。
背后的原因有哪些?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曾提出“富足的原始社会”这个概念。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狩猎采集者只注重满足迫切的物质需求,而没有被过多的欲望拖累。也就是说,狩猎采集者之所以满足了需求,是因为他们仅把需求“限定”在“迫切的物质需求”上,欲望不多。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比今天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更富有,因为尽管后者坐拥财富,却欲壑难填,因贪图更多而显得真正得到的更少。
作者的观点与萨林斯的结论异曲同工。他竭力表明的恰恰是,在许多原始狩猎采集部落中,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驱动力并非当今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源稀缺,而是由于没有过多的欲望,从而拥有大把的空闲时间,过上了我们今天渴望通过努力工作才能过上的那种“丰裕生活”。
为什么欲望低?显然不是因为古今人种不同。“富足的原始社会”有其深层逻辑:狩猎采集社会所发展起来的“资源共享型经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延伸。他们的世界观,坚持人与自然共享资源,延伸到人与人之间,同样必须共享各类物资物品。同时,他们相信大自然是慷慨的,过去一直、现在正在、未来依然会赐予他们食物,没必要杞人忧天、徒增烦恼,无须为储备“多余”而操心。
可是如果食物暂时有盈余,为什么不抓住机会,更加努力工作,以备不时之需?
人类学家詹姆斯·伍德伯恩给出解答。他把以狩猎采集社会为代表的原始社会,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做了一种二元类型的比较:前者的经济形态被概括为“即时回报型”,后者则被称为“延迟回报型”。如果说对自然的慷慨赐予抱有信心,还只是一种观念层面的理由,那么更为坚实的支撑则在于,他们有一套确保食物资源得到平均分配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即“按需共享”的分配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人们都没理由为了比别人积累更多物质财富而浪费精力。
在“按需共享”分配机制下,物质财富平均分配,人与人之间严格平等,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由向他人“索取”的权利。当然,索取不是没有限度的。“按需共享”如何克服需求泛滥或不同需求之间的冲突,需要一套完整的管理规则,包括一些约定俗成的信条、禁令等,从而大体上划定“合理要求”的边界,人们理解并遵循这些规则,便不难确定什么情况下要、向谁要、何时要、要什么,很少提出僭越的要求。
作者深入考察分析发现,努力工作,其实与人类采取农业生产模式带来的文化和经济变革有很大关联。从大历史审视,人类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生产的转变具有显著的革命性,这一转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最重要的是世界观。同时,在客观上迅速增加了人们能够获取和利用的能量。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尽管生产力提高了,但人口数量也增加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农业增产的效果,资源变得更加稀缺。也就是说,随着人口大幅增长,匮乏成为一个常态化的难题,从而放大了人们对资源稀缺性的焦虑。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人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作者揭示了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发展,并非简单的一路高歌式进步,与其相伴的是风险的增加。因此,“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来说,经济问题和资源稀缺性往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唯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更加努力地工作,开拓新的领域”。
“人类向农业过渡最深远的遗产之一是改变了人们体验和理解时间的方式。”在原始社会,狩猎采集者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当下,最多是不久的将来。但生产粮食不同,农民必须同时兼顾过去、现在和未来。“再努力一点,情况会变得更好”“时间就是金钱”……在农业社会,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人都要工作。至此,“即时回报型社会”与“延迟回报型社会”的经济形态区分逐渐清晰:人际关系从人与自然(土地)的关系延伸而来,前者因为大自然同他们分享食物,所以他们也与别人分享食物;后者因为土地需要他们付出劳动,他们便不会无偿同别人分享食物,而是要求支付一定成本。随着历史的发展,“努力工作,创造价值”的观念逐渐被从小就灌输给人们,并演化成为一种良好的职业道德。
按照这一逻辑不难继续推导——历史考察也提供了印证:人类工作史上的又一次大转变,是从进入农业社会以来,特别是进入工业社会后,越来越多的人聚居在城市。作者提出:“只要人们聚居在城市,一种不同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的稀缺性就会塑造他们的欲望。这种稀缺性会激发渴望、嫉妒和欲望,这不是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绝对稀缺性’,而是攀比之中产生的‘相对稀缺性’。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相对稀缺性’是长时间工作、攀登社会阶梯和攀比的内在驱动力”。
永远受制于无限欲望是不正常的,也是可悲的,要医治“欲壑难填之病”。作者不厌其烦地想表明,原始部落不仅提醒我们认识到,现代人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人类向农业过渡以及城市迁移的产物,还提醒我们认识到,要实现更好的生活,关键在于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以便降低物质欲求,用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话说,“我们将再次更看重目的而非手段,更看重美好之物,而非有用之物”。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普鲁斯特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的那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人们期待着痛苦以便工作。”译者周克希说,普鲁斯特的这句话,有一种悲壮的美。今天,我无意也不可能否定努力工作,而是需要不时抽身出来,予以反思,从而有意识地形成历史的合力,构建更合理的生活、更美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