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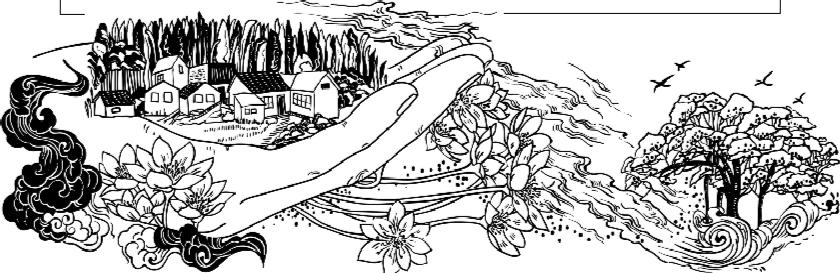
插画 董昌秋
齐 林
对于游子来说,村庄是乡愁的源头。“乡愁”这个词似乎很难形容,不论是席慕蓉在诗中刻画的“一种模糊的怅望”,还是麦卡勒斯笔下混合着孤独的怀旧,都不能精准地对它进行描述。为什么我们会有乡愁?为什么故土让我们魂牵梦萦?说不清,道不明。
我只知道,我的乡愁永远在那个叫查干朝鲁台的村庄里,因为那里有我的母亲,那里有我曾经最美丽的童年。这些年来,村庄一年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唯独查干朝鲁台这个名字,像被时光凝固而成的石头,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查干朝鲁台,汉语意思为“有白石头的地方”,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村子。村庄是宁静的、温文尔雅的。春天,风的声音掠过山坡,一路窃喜着奔向村庄。村庄的声音,从窸窸窣窣的风声开始,从淅淅沥沥的雨声开始,从泥土的气息与庄稼的呼吸开始。那种缥缈的声音,那么生动亲切,把村庄的温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蔓延开来。
早晨,高高低低的炊烟升起,在村庄上空缠来绕去,青黛的远山在乳白色的雾霭中出没,村庄里的红瓦屋脊和蓝色的彩钢瓦在大山的褶皱里与青黛的群山相映成趣,犹如一幅清新的水墨画。
村庄最美的季节是夏天。一种翠绿的色彩,一种鲜活的声音,从每一朵小花、每一棵小草里迸发出来;燕子飞来飞去的姿态,裁剪出村庄的温馨与鲜活。雨季过后,村庄后面的松林里会长出一茬茬的蘑菇,山里人大车小车地来松林里捡蘑菇,好多人家可以卖上数千元。也有那些勤劳的有心人采松花粉,刨黄芩,然后到集市上卖钱。漫山遍野的松林,就是村庄的“聚宝盆”。
农忙时节到了,机耕的轰鸣声让村庄充满希望与喜悦,宁静的村庄也会像遥远城市一样蓦然间变得喧嚣起来。公路上车辆来往,各种机动车呼啸而过,摩托车、农用三轮车、四轮播种车、铲车、大翻斗车、各式小轿车……车轮与地面摩擦过后荡起的声浪飘过树梢,飘向村庄后面的山峦。站在田野里,广阔的大地与天籁和弦,伴着咩咩的羊叫、哞哞的牛叫,鸡犬相闻,村庄就像铺陈于大地上的宽幅农耕长卷。
村庄原本是没有公路的,而现在,查干朝鲁台却被一条伸展向远方的黑色柏油路与城市连接起来。村里来了“第一书记”,他带来了“美丽乡村”项目,国家投资数百万元改变了村庄的环境与面貌。村里的土路换成了坚硬的水泥路,就连我家门前的土路都修建成了3米宽的水泥路。村庄被按下了“美颜键”,村庄中间的主路路面宽阔,一排排太阳能路灯、橘黄色的金叶榆和裁剪齐整的树墙伫立在道路两旁,家家户户临街的门口都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花卉,真是色彩缤纷、争奇斗艳。每隔几十米还修建了垃圾池,村里有专门的保洁人员每天清理垃圾,跟城里的小区没什么两样。夜晚,路灯明亮,文化广场上舞曲铿锵,人们尽情地跳着广场舞,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在旁边嬉戏。村庄,完全可以与城市媲美。
村庄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以至于每一次从城里回来,竟让我不敢相认。
身在他乡,有关村庄的一切都变成珍贵的回忆。在他乡,脑中时常回响起母亲唤我乳名的声音。遥远的村庄,就像一棵根植于心底的老枣树,枝丫参差,红枣盈目。离开村庄的日子,会不由自主地想念村庄的潺潺流水,想念长满了野草与野花的草滩,想念山峦和田野,想念村后的松林,尤其想念儿时的玩伴与乡亲们那质朴的笑脸。虽然人离开了村庄,但心却从来都没有从那个叫查干朝鲁台的村庄里走出来,那里无疑就是游子梦中的家园。
母亲80岁了,一直跟弟弟一起生活。每次回乡,都要听母亲讲一讲村庄里的新鲜事。说完后她都会唏嘘感叹。近几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又回来了许多,他们在政策的扶持下返乡创业了。乡亲们不但温饱无忧,而且生活越来越好了。
每次回到家乡,先陪着母亲吃一顿饭,炕头上,陪母亲说一会儿话,然后,左邻右舍看见我归来,都热情地问长问短,东家叫、西家请,只为喝一杯酒,唠几句家常,让我感受到那剪不断的浓浓乡情。
对一个村庄为什么会如此地眷恋?我终于明白,因为,那是母亲的村庄。离开村庄,回城住上一段时间,虽然有电话,有微信视频,但我还是不经意地想念老家那熟稔的院落,想吃母亲做的饭菜,想坐在温暖的炕头上与她面对面地说说话。
我不停地在城市与村庄之间奔跑,从城市到乡村,再从乡村到城市。但母亲的村庄啊,是我永远无法割舍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