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孙三代制表匠的匠心传承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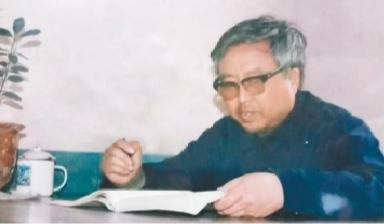
老一代制表匠人滕滨侯在工作中。(资料图)

为赶制滚刀订单,滕栩林(左一)和儿子滕振宇正在研究制作工艺细节。工作中,父子俩总是配合默契。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摄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核心 提示
在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个家庭,祖孙三代都是制表匠人。爷爷滕滨侯是表厂建厂的第一批老工人,被称为“模具大王”;父亲滕栩林多年来自主研制滚刀,使企业成功实现滚刀替代国外进口;作为第三代,90后的滕振宇不仅技术过硬,而且已经走上管理岗位,现任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工具厂副厂长。
采访滕栩林,是在一个周日的午后。此时,年近六旬的滕栩林已在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工具厂连续加班半个多月,而他的儿子滕振宇作为工具厂副厂长,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滕栩林骄傲地告诉记者:“我们家祖孙三代制表匠人,见证了辽宁手表工业的兴衰与崛起。”
“咬牙坚持不放弃”,是老辈匠人、滕栩林的父亲滕滨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一天,24小时,只为稳稳的86400秒,滕家三代人像指针一样已经在孔雀表业精准“转动”了大半个世纪,践行并传承了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
铭记于心的是匠心坚守
“不能半途而废,什么都有个过程,咬牙坚持不放弃,一定会成功。”在滕栩林的记忆里,父亲滕滨侯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他曾经说的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滕栩林的脑海中。
多年来,这句话就像一只大手,始终在背后推着技术攻关中的滕栩林不断向前,也成为滕家人潜心钻研制表技艺的制胜“法宝”。
“小时候,父亲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忙,我几乎见不到他。”已经去世十几年的滕滨侯,在滕栩林的记忆中总是板着面孔,在家的时候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不知在琢磨着什么,谁都不敢打扰他。回想起父亲留在他记忆中的零散片断,滕栩林才发现,在尘封的生活琐事里,满是父亲对制表技艺的执着。
偶尔下班回家早的时候,父亲会从饭盒里拿出留给滕栩林的一大团白米饭,或是一小堆单独挑出来的肉,让滕栩林感受到浓浓的父爱。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敢在父亲面前多晃悠晃悠,享受父子间难得的亲近。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滕栩林从小就爱自己动手摆弄一些小零件。有一次,他把家里的小闹钟拆开却怎么也装不上了,吓得他把弄坏的闹钟藏了起来,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再拿出来研究一番,却始终无法恢复如初。于是,他把闹钟暂时放在一边,又开始琢磨用磁铁和铜丝连接收音机的耳机,几经折腾竟然真让耳机发出了“吱吱啦啦”的声音。
一天傍晚,享用完父亲给他留在大饭盒里的饭菜后,滕栩林拿出自己制作的磁铁线圈小耳机,在父亲面前显摆。滕滨侯看到滕栩林鼓捣出来的“小玩意儿”,露出难得的笑容。看着父亲心情不错的样子,滕栩林趁机拿出被自己拆废了的小闹钟向父亲求助。父亲没有责怪滕栩林,而是和他一起把闹钟重新装好。看着父亲专注的神情和调试闹钟时灵巧的双手,滕栩林那一刻真正感受到父亲是一个手艺精湛的钟表匠人。
丹东是中国钟表制造业的发源地之一,始建于1957年的辽宁手表厂,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鼎盛时期。那时,中国大地刮起了孔雀表的抢购风,经历了一表难求的辉煌时代。
在那个年月的丹东市,许多人都以在孔雀表厂工作为荣,更何况滕栩林的父亲滕滨侯还是表厂的“模具大王”。
始终不忘的是工匠初心
在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工具厂的刀具生产车间里,记者看到正在铲磨床边忙碌的滕栩林,一个不足半个小拇指甲大小的超薄机芯滚刀即将在他的巧手里诞生。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制表行业中模数最小的刀具,滚刀最小模数要求0.036。”看着停留在滕栩林食指肚上的滚刀,借助放大用的寸镜才能看清它如头发丝一样纤细的齿型,双眼累得发红的滕栩林告诉记者,“这样的滚刀我们自己能做了,以后公司研发高品质机芯就不会再受制于人。”
超薄机芯滚刀是滕栩林利用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通过改变传统加工工艺,历经2个月反复加工试制,于2019年12月30日生产研制成功的,符合瑞士高端技术标准,达到国内顶尖技术水平。滕栩林的成功,让孔雀表业向“国表用国芯”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别看加工制作只用了两个月,但琢磨构思的过程早在2002年就已经开始了。”滕栩林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才真正体会到父亲作为一个手表制作匠人的喜忧,“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年一回到家里就闷在屋里不说话,母亲也不让我们打扰他,是因为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琢磨模具的制作与创新,当我有了同样的经历后,终于明白父亲当时的沉默与思索。”
滕栩林指着眼前六七台机床告诉记者,做一把滚刀需要四五道工序,如果在最后一道工序上出现失误,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很多刀具工匠因为克服不了挫败感,放弃了这份职业。“我18岁进厂当学徒,一干就是40多年。”滕栩林也想过放弃,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是因为他的父亲滕滨侯。“父亲告诉我,咱们做技术的比其他人更需要毅力,过硬的技术是靠时间积累和沉淀的,坚持不放弃,才能获得成功。”滕栩林回忆道,“父亲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让我咬牙熬过了困难期。”
在经历了制作滚刀时的无数次失败和最终的成功,滕栩林同样感受到了父亲在遇到难题时的沮丧和突破难题时的喜悦,也读懂了父亲说的“咬牙坚持不放弃定会成功”的真正含义。
有了更好的工具,才能制作出品质更好的手表。如今,滕栩林制作的新滚刀成功率达到90%以上。他的成功,为国产机械表注入了强“芯”剂,也让孔雀表业实现“国表用国芯”的目标不再遥远。
矢志不渝的是国表用国芯
在滕振宇的幼年记忆中,最清晰的是家里高高挂在墙上的爷爷滕滨侯的那把巨大的画图尺。在他看来,那是爷爷的“珍宝”,轻易不让家人碰。只有在高兴的时候,爷爷才会把滕振宇抱起来,让他轻轻摸摸。
渐渐长大后,滕振宇终于明白,那把画图尺在爷爷的心中代表着他的制表事业,珍视得不容触碰。
现在,滕振宇在自家的阳台上,也腾出一个小角落,存放他制作模具时使用的各种工具。拉开抽屉,螺丝刀、钳子、镊子……一样一样摆放得整整齐齐,这里也是他3岁女儿不能碰触的“禁地”。
祖孙俩用同样的方式热爱着自己的制表事业,任岁月长河无尽流淌,制表匠人的匠心矢志不渝。
2008年7月,辽宁手表厂经过重组改制,投资建成了辽宁手表工业园。新组建的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升级提升企业内功,重新找到市场位置,励志建设成为机械表机芯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
2009年,滕振宇伴随着孔雀表业改制的步伐进入公司,并跟随孔雀表业一起踏上了革新之路,很快成长为不断创新求变的新生力量。
继承爷爷的衣钵从事模具制作,绝对不能给爷爷丢脸,在滕振宇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激励自己。
工作了11年的滕振宇热爱这份事业,他坚信未来的匠人一定是既懂管理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于是,他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去。
2016年,滕振宇担任了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工具厂模具班班长,开始接触管理工作。因工作业绩突出,2018年4月,滕振宇被提拔为工具厂副厂长。
在工作中,滕振宇负责公司工具厂的刀具、模具等生产车间的协调运转,成了父亲滕栩林的领导。
“滚刀生产一般都是急活儿,时间短,任务重,丝毫不能耽误。”滕振宇告诉记者,为了工作不打折扣,父子俩尽量协调好“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生活中,他是父亲,叫我干什么,我都得尊重他;工作中,作为父亲的领导,给他派任务,甚至占用他的休息时间安排工作,父亲都是随叫随到,全力支持我。”聊到工作,不善于交流的父子俩倒是配合默契。
“赶订单需要帮助时,振宇尽最大努力全力调度,从未因为任何原因影响生产进度,他当我的领导,够格!”对制表技艺要求几近苛刻的滕栩林,对儿子的管理大加赞许。
身为副厂长的滕振宇如今兼顾生产和管理,在他身上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以及对钟表事业的热爱。目前,他正带领团队着手研究“极进模”的结构,“将来的手表制造工业对模具的精度要求会越来越高,父亲跟我说过,不论什么时候,制表工匠的手艺不能丢。”
让中国的品牌手表都有一颗中国“芯”,不仅是滕家祖孙三代矢志不渝的目标,亦是所有孔雀表业制表匠人的目标。
补记
工匠精神
无论是滕滨侯说的“咬牙坚持不放弃”,还是滕栩林口中的“手艺不能丢”,再到滕振宇理解的“百分百做好工作”,对滕家三代制表匠人而言,工匠精神就是“一辈子坚持做好一件事”。
工匠精神不仅使滕栩林受益,也深深影响着滕振宇。在滕栩林眼中,儿子是个勇于迎难而上接受挑战的人,有着年轻人特有的冲劲儿。2009年7月,滕振宇在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工具厂开始了为期14个月的基层工作——制作模具,也就是传承爷爷滕滨侯的手艺。巧的是,滕振宇的师傅魏守义刚好是滕滨侯的徒弟。
“爷爷给我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厂里很多老制表匠都是他的徒弟,每当我在技术上遇到困难,这些老师傅都会帮我,这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滕振宇切身感受到每一位老匠人对后辈的无私传授。
滕振宇记得,他在对工具厂机械加工部门进行改革时,决定把两个部门合并成一个部门,没想到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到生产效率,工时改革不得不提上日程。有限的时间里究竟能出多少产品,数量如何明确规定,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着他。
此时,滕振宇想到了已经退休的师傅魏守义。魏守义从模具结构等专业技术方面给滕振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他解决了大难题。经过改革,如今的库存在极限状态下也能有两个月的备品,不会再出现“无米下锅”的情况。
“(钟表)时针好不好,时间会证明。”2002年,第一块孔雀牌陀飞轮手表问世。10年后,孔雀表业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陀飞轮机芯,双陀位置分别在5点位和7点位。在我国,孔雀表是唯一能够做出这个点位双陀飞轮机芯的品牌;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孔雀和罗杰杜彼能够生产此款双陀飞轮手表。
一路走来,艰难跋涉,滕家三代制表匠人正是始终坚守着这份工匠初心,见证了盛极而衰的辽宁手表制造业的再次崛起。
走过昨天,经历今天,期待明天。如今,已经掌握尖端滚刀制作技艺的滕栩林,把目光转向了下一代,“儿子现在从事模具制作,我希望他还能把我的滚刀制作技艺传承下去。”
同时,滕栩林还在物色更出色的徒弟,“祖祖辈辈留下的手艺要是没能传下去,心里怎么能过得去呀。”
说到底,匠人并不是心疼自己,他们更心疼这门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