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流行织金服饰 对后世影响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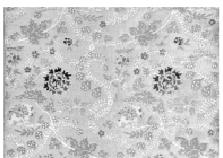
缠枝牡丹金宝地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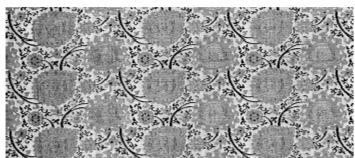
白地织金胡桃纹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世祖(中)穿红色质孙服。

元代纳石失织金锦男式袍服。

辽博展出的文物战“疫”海报。

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织锦仪凤图》。
本报记者 商 越
核心提示
“文物系荆楚 祝福颂祖国”接力海报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其中一幅“有凤来仪,山河无恙”文物海报,展现的是《织锦仪凤图》中的凤凰图案,透过这件文物,能领略到元代精湛独特的织金锦工艺和尚金习俗。元代统治者调集西域、江南、中原各地能工巧匠,组建庞大的官营作坊,从事织金锦生产,中国织金技术由此进入鼎盛时期。绚丽的服饰文化凸显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对后世纺织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雀羽线和金线织就华丽金锦
“文物系荆楚 祝福颂祖国”接力海报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其中一幅“有凤来仪,山河无恙”海报,展现出元代精湛独特的织金锦工艺和尚金习俗。同时,在文物战“疫”活动中,传递出祝福祖国、祈盼百姓安康的文化信息,寄托了辽宁文博人对祖国的深切祝福。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馆员袁芳向记者介绍,《织锦仪凤图》是辽博馆藏一级文物,是一件织锦。它纵54厘米、横5.5米,共有两组连续图案,以凤鸟为主体,其他鸟类、花卉,散点式分布,鸟类造型优美,配色华丽,制作非常精美,掺和使用了丝线、金线和孔雀羽线,织出凤凰和百鸟纹样,可以看出当时织造技巧和制作者的独具匠心。
袁芳解释,孔雀羽线是织绣中的一种特殊材料。它选取孔雀尾巴上的翠绒,以丝线为线芯,将丝线和孔雀羽丝捻合,精心加工而成。孔雀羽线不褪色,在光的折射之下,不同的角度还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这种孔雀羽线异常珍贵,在明清时期,多用于织绣皇帝或王公贵族袍服上的云龙纹。
这幅织锦还采用了元代最具代表性的织造方式——捻金线技术,即在丝织品上通过多种方法加金,形成织金锦,有捻金(搓金线)、印金(泥金印花)、片金(缕金丝织)、拍金(又作箔金,与现代贴金相似)、销金(包括印花、描金、点金等)以及用于刺绣上的平金、盘金和蹙金等数十种。此锦用金线勾勒鸟羽、树枝、花朵的线条,显得画面金光闪闪、雍容华丽,令人赏心悦目,体现了华贵典雅的艺术风格。
“图案展示的是百鸟朝凤的故事。”袁芳说,百鸟朝凤图案被广泛应用在百姓的生活中,寓意着吉祥、和谐、美满。
这件《织锦仪凤图》原为清宫御书房藏品,后由北洋政府官员、工艺美术家朱启钤收藏。十九世纪20年代末期,朱启钤转让给张学良,后来归藏于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
元代有庞大的织金锦官营作坊
我国唐代织物中已有用金的痕迹。唐文宗时期,宫廷贵族妇女就将织金锦运用到服饰中,唐晚期捻金线开始广泛运用到刺绣上。研究发现,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黄金有着特殊的喜好,不仅因为它有着金光灿烂、耀眼夺目的外表,还因为它代表着坚韧的品性。蒙古族、契丹族、女真族的达官贵人都崇尚衣着用金,并以此显示他们的财富、地位与时尚。女真族建立政权后,因其民族喜爱用金,促进了织金锦的广泛应用,并逐渐形成社会风气,发展出多种织金技术。蒙古人沿袭金人的尚金习俗,使元代成为织金锦的鼎盛期。
织金锦,蒙文中称为“纳石失”(也称纳失失)。
因为元朝统治者的官服以及帐幕等多用织金锦缝制,为了满足统治者对织金锦的大量需求,在统一中国的征战中,蒙古军队俘虏了大批江南丝织匠人、阿拉伯织工,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织造织金锦的高手。
为实现规模化生产,元朝设立了官营纺织业作坊——金锦局,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供应官员消费而生产的机构,主要由工部和将作院管理;另一类是专为后宫或贵族生产的机构,如为皇后设的中政院、为太子设的储政院、为太后设的徽政院下辖的生产机构。在《元史》中有明确记载的官营机构中,归属工部的主要有两处,即设在大都(今北京)的别失八里局和纳石失毛段二局;归属储政院的有两处,即弘州纳石失局(今河北张家口市阳原县)和荨麻林纳石失局(今张家口市洗马林镇)。《永乐大典》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说明:“至元十五年(1278年)二月,隆兴路总管府别都鲁丁奉皇太子令旨,招收析居放良等户,教习人匠织造纳失失,于弘州、荨麻林二处置局。”“秩从七品,二局各设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弘州和荨麻林是重要的官府纺织中心。据《元史·镇海传》载:“先是收天下童女及工匠,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命镇海世掌焉”,征集各地能工巧匠,并由成吉思汗时期的功臣镇海执掌,这说明弘州局不仅工匠数量众多,而且民族构成多样,来源区域广泛,包括被蒙古族统治者先后征服的汉人、回鹘、女真等民族,且规模庞大。中统三年(1262年),朝廷下令“徙弘州锦工绣女于京师”,显然是要引进弘州织造技术充实大都,说明弘州织匠技术水平相当高超。
荨麻林纳石失局也有很多西域迁来的工匠。据《元史·列传第九》记载:“至太宗时,仍命领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从西域迁来的3000户工匠,如果按每户4人计算,就是1.2万人,全部从事纳石失的手工业生产,规模相当可观。可想而知,当时这些不同民族的工匠被安置在一起,相互交流,共同促进了中西方织金锦技术的提高,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北方丝织物在织造及纹样上都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
加金服饰只限王公贵族、文武百官等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讲述了元代贵族服饰:“衣金锦及丝绢,其里用貂鼠、银鼠、灰鼠狐之皮制之……”“大汗于其庆寿之日,衣其最美之金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衣同色之衣,与大汗同。”每年在大汗的生日宴会上,忽必烈和贵族们都穿着这类饰金服饰参加盛典,而金带、金锦衣等加金的服饰用品还常常被大汗作为赏赐品赠予大臣。《马可·波罗行纪》第88章记载,“每年并以金带、袍服,共赐此一万二千男爵,金带甚丽,价值亦巨,每年亦赐十三次。”
这些用料贵重、织造费时的纳石失,使用范围也极讲究,只局限在皇室贵族、文武重臣等地位尊崇者之间。元朝政府明令禁止民间穿用金银,并以加金量来显示身份与地位。在《元史·舆服志》中规定:“职官除龙凤外,一品、二品服浑金花,三品服金答子,四品、五品服金袖,六品、七品服六花,八品、九品服四花。”“命妇衣服,一品至三品服浑金,四品、五品服金答子,六品以下惟服销金,并金纱答子。”
浑金花或浑金,是指全部以金线织成的浑金缎制成的服装;金答子是指部分装饰有块状金花的丝织物;金袖则是只在袖子上装饰金花。元代织金锦的盛行,改变了唐代以多种色彩为主的配色风格,形成以金银色为主的配色特点。其织锦的纹饰,疏密有致、层次丰富,多用龟背、宝相花、如意云、鸾凤等题材,呈现出装饰风格。
除了用作服饰衣料,纳石失也常用于内廷大殿寝宫日常起居的帷幔、被褥、椅垫、靠垫以及皇帝出行的舆辂、仪仗等。
元朝因为疆域辽阔,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使东西方交往空前频繁,商队络绎不绝,西域文化及其装饰纹样、手工技艺不断传入中原,因此,这一时期的染织纹样留下游牧文化、西域文化和传统文化交融的印记。到了明代,宫廷中仍然大量使用金线加工服饰和纺织品,捻金技术再次改进提升,金线由粗变细,直到清代。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史记
SHIJI
“质孙服”直接被明清两朝继承
辫线袍是元代最为流行的男子服装,窄袖束腰,上身合体,下摆宽大,属于上衣下裳相连的袍裙式。《元史·舆服志》载:“辫线袄,制如窄袖衫,腰作辫线细褶。”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腰间折褶或缝缀用编辫子的方法编结成的辫线,因而得名辫线袍,这种款式便于骑射活动,手臂灵活自如,还保护内脏和腰背。
元代在辫线袍的基础上,衍生出来一种质孙服,是参加宫廷盛宴“质孙宴”必须穿着的特定服饰。“质孙”是蒙古语“华丽”的音译。《元史》载:“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廷大宴则服之……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也就是说,只有受赐者才有质孙服。“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有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这种质孙服相当于一种礼服,面料主要是元代最具特色的织金锦,必须是衣、帽、腰带、鞋配套穿戴,并且在衣、帽、腰带上饰有珠翠宝石,做工精细,且按身份、地位严分等级:“天子质孙,冬之服凡十有一等”“夏之服凡十有五等”,其他百官的质孙服则冬服分九款定色,夏服有十四款定色。
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述,元代统治者每年要举行13次大朝会。每逢朝会时,帝王、大臣、亲信穿同一色的质孙服,上面点缀有珍珠宝石,在大殿前用金杯按爵位、亲疏、辈分频频祝酒,气氛热烈,场面壮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世祖出猎图》中,元世祖忽必烈外罩的白皮袍下,即穿着一身红色质孙服。
明朝统治者发现质孙服有穿着舒适、活动自如的优点,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明太祖朱元璋将质孙服全面继承,制定其校尉(武官官职)服饰。《明史》载:“令校尉衣只孙,束带,幞头,靴鞋。只孙,一作质孙,本元制,盖一色衣也。”可见明代的校尉服就是参照元代创制的质孙服。在明朝权贵的推崇下,质孙服成为流行款式,在民间广为流传。直至后来清代的官服,我们也能够发现袍裙式、辫线、褶裥等元代质孙服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