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访“荷马”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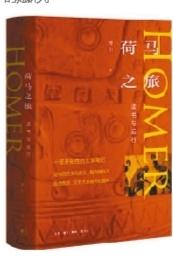
牛寒婷
提示
2002年,年近八旬的理由将目光投向一些“遥远而陌生的东西”,此间,他生出困惑,作为诗歌的国度,我们为何乏有史诗?他开始重新翻看《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接着,又数次远渡,前往雅典、特洛伊等地考察寻访。4年后,理由写出《荷马之旅》,通过对所踏之地宏阔地理、人文及历史现实氛围的回望分析,着重深描史诗原发地环境因素对西方文化模式形成的作用,并从文明流变的凝视中,解读希腊文明对世界文化的赋形。
每晚,我都与儿子共享睡前的阅读时光。随着阅读习惯的逐步养成,大多数时候,都是儿子自己看绘本,无须我再声情并茂地充当故事朗读机。不过,他有时也会好奇我读什么。比如最近我手里这本《荷马之旅:读书与远行》,书中那些精美的插图就让他爱不释手。在专注地研究了一番扉页上的荷马后,他忽然问我此人是谁。“他就是盲人荷马呀,讲木马计……”虽然在意识到什么后我已马上闭嘴,可小家伙还是适时地提出了重温木马计的合理要求。
之所以说起这件小事,是因为在《荷马之旅》中,我读过一个这样的段子:这本书的作者理由在启程探访特洛伊古迹前,曾在北京参加过一个艺术家的沙龙聚会,当朋友问他最近忙什么时,他回答说在看荷马。“河马?”朋友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去动物园?”……这让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不仅如此,作者添油加醋的夸张描述,还让我突发奇想:用儿子演练一次“荷马”与“河马”的游戏如何?这真是个不错的想法。
阅读的故事
误“荷马”为“河马”的笑话意味深长,它把一个想象中的画面勾连了出来:古典书籍被束之高阁,落满灰尘,无人问津。理由说,这大概是因为荷马史诗既非显学,读来又费劲,即便在中国文学界也难遇知音。现代人的阅读一如行事,大多讲求实际效用,趋利避害求易躲难,荷马被抛进故纸堆在所难免。可另一方面,古代典籍之为经典,又在于它的魅力难以抗拒,一旦不期然地与之邂逅,或是误闯了它的门禁,那么,即便是再偏僻的冷门之物,也可能成为钟情的珍宝。
理由便是这样的幸运之人。一个炎炎夏日的午后,在书架中备受冷落的区域,他邂逅了《伊利亚特》:“神圣的缪斯啊,请歌唱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狂怒吧,这怒火招致了巨大的灾祸,给希腊人带来万千种苦难……”这广为后人传诵的伟大史诗的开篇一下就攫住了他,也开启了他的荷马之旅——可这一起步,足足耗去了他4年的光阴。席勒曾说,他打算用三天时间读完《伊利亚特》,如果没有阅读经验的两相对比,这也许会被视为夸口。但理由的确只花4天,就读完了汉译的《伊利亚特》,又读《奥德赛》用去3天,不仅如此,有关荷马和古希腊研究的各种著述,还很快占满了他一个书架。
阅读的速度暗示了阅读的沉溺与痴迷程度,而从史诗文本到荷马研究再到古希腊著述的涉猎,则说明理由掉进了古典文明的巨大漩涡。不难猜想,当最初的3分钟热度渐渐冷却,一定还有什么在支撑着他持续而又快速的阅读:或许是一种心志坚定的热爱,或许是阅读的某类困惑与迷思,又或许,那是有待完成的一项任务。丰富有效的阅读催生思考,不间断的思考又催促着马不停蹄的阅读者去追异逐新。大数据时代为链接式阅读提供了便利,铺天盖地的书讯动态正是眼花缭乱的目标,心无旁骛的猎人专注地对它们进行检索、比较和筛选,在扣动扳机前,将选定之物“一网打尽”、揽入怀中的信心与信念早已充盈心间。
在读完半个书架、仍有半个书架等待浏览时,理由从书堆之中抬起头来,像最初邂逅荷马的那个午后一样,冲动与渴望再次将他俘虏,敦促着他开启了时空中的荷马之旅。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沿着荷马史诗的路线,理由对爱琴海周边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踏访,就像书斋中的他一本接一本地阅读。身与心的双重游历激发了写作的欲望,《荷马之旅》便由此诞生。只是,对于古稀之年的理由来说,无论读书写作还是实地考察,过程都不无艰辛,就更不要说那常常折磨他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了。然而,正是这不可抗拒的对时间的焦虑,成为写作的最大动力,支撑了他近乎疯狂的阅读与行走。
文化的迷与思
作为东方人,沉迷在古希腊的世界里,追溯和探察西方文明的源头,理由很自然地会将它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在他看来,中国殷商时代与荷马史诗的背景迈锡尼时代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属于青铜器时代中晚期,都有征伐不休的军事组织,都有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等等。不过,比起这些表面的相似,海洋与大陆文明的天渊之别才是有趣的看点。
古希腊那闻名世界的体育和文艺赛会,是希腊民族独有的祭神活动,它在神的幕布之下,展示的是人的舞台,理由由衷赞美它所彰显的希腊人对卓越与自由的尊崇与追求;而在殷商这样的东方国度,则“根本不准许有希腊那般规模的自由聚会,统治者总是以恐惧的心理钳制公众的社会生活以防患于未然,并直接导致民众身心的弱化”。在谈到爱琴文明的流动特征时,理由敏锐地看到了迁徙活动与自由精神互为因果的奇妙关系,并一语道破了它触发早期知识启蒙运动的积极意义;而殷商社会的子民,则必然与米利都集市上那些平民思想者互不相识、如隔天渊。
但有时候,对古希腊文化的认识不乏真知灼见的理由,也会落入比较的窠臼之中,他会不自觉地用东方视角去审视西方,从而造成思想和表述上的矛盾与混乱。比如,他用伪善的东方道德标准,去嘲笑希腊诸神的“人性弱点”,而这早已是陈词滥调;再比如,他虽然陶醉于荷马笔下的英雄世界,却又爱犯现代人以今断古的毛病,无限放大早期人类社会的原始蛮荒特征,认为那是“人性裸露”“未经理性洗涤与道德驯化的年代”,这自然让他无法更好地领会荷马史诗的人文主义和智性特征。这些因阅读而生的迷思,若想破解,恐怕还得回到阅读,曾让理由废寝忘食的那一架子书籍——比如他在书中援引的学者基托的《希腊人》和芬利的《奥德修斯的世界》,恰好能在人性的问题上为他指点迷津。
对我而言,阅读《荷马之旅》是件愉快的事,这不仅因为我是彻头彻尾的希腊迷,还因为借由它,我开始了自己的荷马之旅。合上理由的书时,《伊利亚特》我已读了一半,在想象诸神与英雄世界的那些美妙时分,理由描述的奥林匹斯山的绝妙景色让我陶醉——“常年云雾缭绕,雨季电闪雷鸣,冬日可见山头积雪,白若玉冕,雪吻蓝天”。而恰在这时,正画画的儿子,在一旁的桌边喃喃自语:“这是活火山,在希腊的北边……”我放下书走到儿子的身旁,“用长着翅膀的话语”——这是荷马最爱用的一个比喻——轻声对他说:“在希腊北部,的确有一座平地而起、高耸入云的山峰,那里是俯瞰世界的众神的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