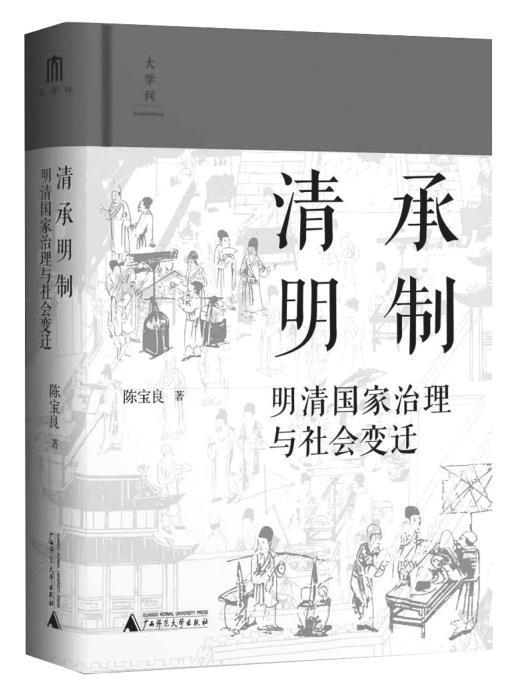
尤鉴
■提示
陈宝良教授的《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是一部打破传统政治史框架、以社会史与文化史视角重构明清历史叙事的创新之作。其学术深度与叙事魅力相得益彰,勾勒出一幅跨越朝代更迭的“大历史”图卷,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重新理解明清社会的窗口,揭示出明清两代在社会治理、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层连续性。
《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清承明制》)以“清承明制”这一经典命题为切入点,却并未止步于制度层面的承袭与变革,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俗社会,通过鲜活的社会群体、流动的世风世情、繁复的地方治理实践,勾勒出一幅跨越朝代更迭的“大历史”图卷。这部著作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论著,又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通俗读本。
传统史学对“清承明制”的讨论多聚焦于政治制度与皇权强化,例如清代内阁对明代内阁的继承、军机处对皇权的极端集中等。陈宝良则另辟蹊径,将“制”的范畴从典章制度扩展至社会运行机制,揭示了明清两代在社会治理、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层连续性。
《清承明制》中对“镖局”起源的考证颇具代表性。明代的“镖客”因商人旅途安全需求而兴起,至清代演变为职业化的“镖局”,其名称从“保标”到“保镖”的流变,既反映了商品经济下社会分工的细化,也暗示了明清两代治安问题的延续性。这种从“制度溯源”到“社会功能”的视角转换,让读者看到“清承明制”不仅是政治体制的继承,更是社会需求的自然延续。
作者对“幕府人事制度”的梳理同样精彩。明代幕僚多由科举失意的文人担任,清代则进一步形成专业化、层级化的幕宾体系。这种“佐治检吏”的群体,既是皇权下地方治理的工具,也是科举制度“溢出效应”的产物——大量无法通过正途晋升的读书人,以幕僚身份参与社会治理,成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间阶层”。这种分析从社会流动与知识群体生存状态的角度,揭示了制度变迁背后的世俗化动力。
陈宝良笔下的明清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世俗化世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思想解放的暗流,共同推动着社会从“礼法秩序”向“世俗生存”转型。书中通过部分群体的命运浮沉,生动展现了这一过程。
“富不教书”的塾师、“清客帮闲”的文人、“侠客化”的僧人,这些群体在传统史学中往往被忽视,却是明清社会世俗化的缩影。明代科举制度的僵化催生了庞大的落第文人群体,他们或投身幕府,或成为讼师,甚至混迹市井,以知识技能谋生而非“治国平天下”。这种职业分化不仅反映了科举制度的失效,更揭示了知识阶层从“士大夫”向“职业人”的身份转变。
天地会、镖局、会馆等组织的兴盛,标志着民间社会力量的崛起。作者表示,这些组织虽被官方视为“隐患”,实则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产物。例如,清代会馆从同乡互助组织演变为行业垄断机构,既填补了官方治理的空白,也加速了商业资本的聚集。
陈宝良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儒林外史》《水浒传》等文学作品视为“社会史档案”,以文证史,捕捉文学叙事中的世情百态。书中对“阴曹地府的诉讼”“僧人的侠客化”等主题的解析,既充满文学趣味,又具有史学深度。例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地府的桥段,被作者解读为明代民间对司法不公的隐喻。阴司诉讼的荒诞情节,实则是现实社会中“好讼”风气的投射——明代江南地区诉讼成风,甚至出现职业讼师群体,这种“以阴讽阳”的文学手法,成为观察世俗社会的重要镜像。
《清承明制》中引用《十叶野闻》中镖客与盗贼斗法的故事,揭示镖局行业的江湖规则:镖客不仅需武艺高强,更要深谙人情世故,通过“递帖子”“拜码头”等方式与黑白两道周旋。这种“以小说补正史”的方法,让历史叙事更具血肉,也凸显了世俗文化对制度运行的渗透。
陈宝良的写作始终贯穿着对现实的观照,反映了历史书写的当代性。书中对“谣言传播”的分析尤为深刻:从明代“倭寇来袭”的恐慌,到清代“选秀女”引发的民间婚嫁狂潮,作者认为,信息不对称与权力结构的失衡,是谣言滋生的温床。
作者对“清承明制”的辩证解读,也为理解历史连续性提供了新思路。清朝虽以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却在社会治理层面大量沿用明制,甚至将明代后期的世俗化趋势推向高潮。这种“继承中的创新”提示我们:历史变革往往不是断裂式的颠覆,而是层累式的调适。
这是一部“接地气”的学术典范之作。《清承明制》实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完美平衡。陈宝良以“小人物”的命运为经,以制度与社会的互动为纬,编织出一张覆盖明清两代的世俗化网络。塾师的清贫、镖客的江湖等细节共同构成了一个真实可感的“人世间”。
《清承明制》提供了一种“向下看”的历史观——真正的历史动力,往往藏匿于市井巷陌、众生百态之中。正如作者所言:“继往”方能“开来”,唯有理解世俗社会的韧性,才能读懂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