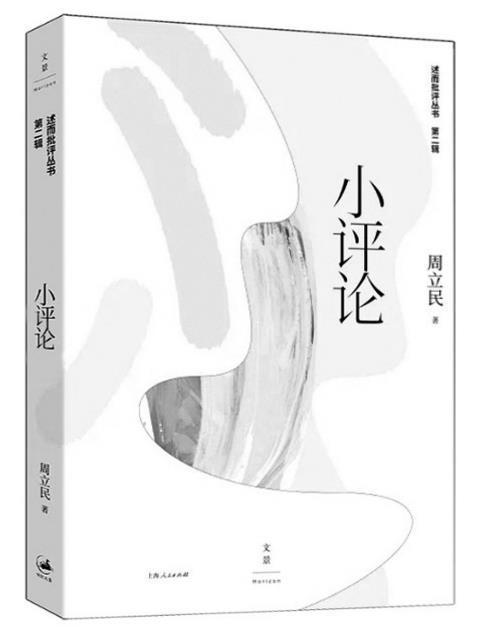
周立民
读理查德·艾尔曼的《乔伊斯传》,里面写到《尤利西斯》最初是发表在一份名为《小评论》的杂志上,这份杂志由玛格丽特·安德森和简·希普两位女士主编,“这家刊物更倾向于创新,以发表散文为主”。(【美】理查德·艾尔曼:《乔伊斯传》第480页,金隄等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版。)她们欣赏乔伊斯的创作,面对社会各种压力都不屈服,后来为这部杰作还上过法庭。我们不必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去赞赏她们的眼光,至少可以说她们对这部作品和作家的捍卫是尽心尽力的,也可以说是爱和欣赏吧。
当年看到过《小评论》的刊名时,我就曾想:真不错,将来拿它做一个书名。我设想中的“小评论”,可长可短,以精短为主,用随笔或札记的形式写出,既是作品品评,也是我的心境自述。文字要闲,却又不乏锐利……
据说,“庞德先生曾数次就美国大学里的学术研究坦率地发表意见,批评它死气沉沉,指出它与真正的文艺鉴赏和富有创意的文学生涯是多么隔绝。他始终准备着与学究作风相对抗。”(【英】托·斯·艾略特:《埃兹拉·庞德的韵律与诗作》,苏薇星译,《艾略特文集:批评批评家》第20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版。)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吧,况且庞德后来还被医生鉴定为精神失常送进了精神病院,自然是不经之论。不过,今天仍然很流行的艾略特在谈庞德的诗歌时,说过这样的话:“有个肤浅的测试认为原创性诗人直接走向生活,次生性诗人直接走向‘文学’。探究此事,我们发现真正‘次生性’的是将文学误作生活的诗人,而他经常犯此错误的原因无它——阅读不够。”(【英】T·S·艾略特:《引言》,《涉过忘川:庞德诗选》第41页,西蒙、水琴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3月版。)我想置换一下,把这里的“诗人”置换为批评家,次生性批评家让批评走向“学术”。批评和学术并非天然对立,互不相容。比如,写学术论文要求克己,最大限度地让“我”躲在“客观”的皮夹克之下,而批评之所以有活力,恰恰是这种文字里,“我”的鲜活可见。在某些时候,我并不认为批评是对作品判断、检讨、“指点”,它更是对话、交流,甚至是评论家以作品为素材的自我表达,这才是它更有魅力之处。
“小评论”应当是我下一本评论集的名字,这里被我偷懒提前使用了。偷懒的背后还有一种惫懒的心绪。这些年,我所写的当代文学评论的文字越来越少,我从不否认当代不乏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我也不曾远离他们,只是不在那些热热闹闹的文学“现场”,而在我安安静静的书斋里、在作家的书本之间。我更愿意隔着书本与作家交流,更愿意躲进小楼成一统,谈一点对那些不曾轰轰烈烈的作家的感想,与“流量”远一点的“小评论”,却真实地出自我心。
鲁迅编完自己的集子后,曾说:“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我也奢望为“小评论”留一点空间,寄存我并不想争一日之长的闲心。我不揣浅陋把这些新新旧旧的文字编在一起,梳理它们的心态与鲁迅编《坟》时的感觉可能很接近:“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鲁迅:《坟·题记》,《坟》第2页。)
我也想做一个纪念,纪念我走过的时光,纪念曾在一起的人和事,纪念一种自由和任意的心态。特别是我看到其中有一篇为谢有顺的随笔集所写的书评,那是20多年前,回想意气风发的谢有顺和那些时光,我有那么多感慨;今天重读收在书里的一些文字,我为自己当年的坦率、无所顾忌而惊讶。倘若它们伤害过谁的话,我请求原谅,请接受我的真诚和理解曾经的热情。
前年,鲁迅作品单行本重印时,我请出版社的朋友寄了一套给我,有别于厚重的全集本,这两年,我断断续续地闲读起来。人过中年,再读鲁迅,读出他的忧伤和沉重自然不稀奇,在这之外,我感到的不是冷,而是热,是温暖和坚毅,比如这一段:“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鲁迅:《坟·写在〈坟〉后面》,《坟》第298页。)先生说得多好啊,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它也鼓励我,有一天我还是要把那本真正的“小评论”写出来,这正所谓“哀莫大于心不死”吧。